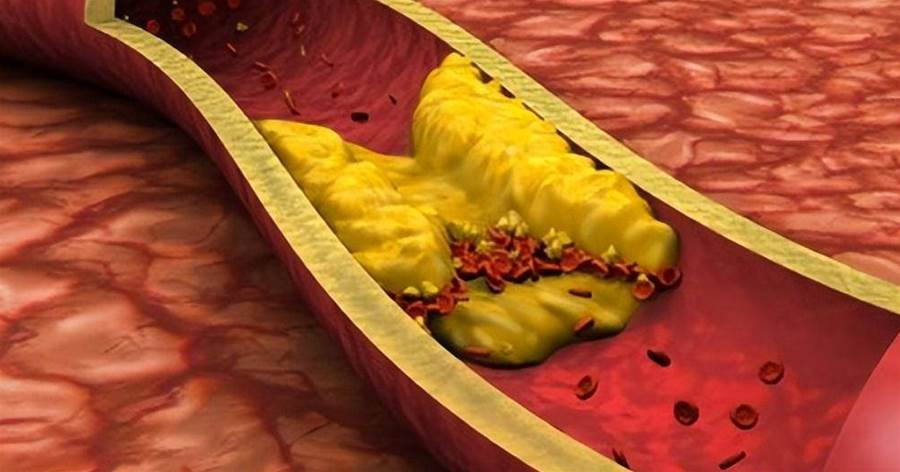《阿公的修理哲學》
阿公的工具箱是個神奇的百寶袋。生鏽的鐵鎚、纏滿膠帶的螺絲起子、用橡皮筋綁著的老虎鉗,每樣工具都有它的故事。小時候我最愛蹲在阿公腳邊,看他用這些老夥伴把壞掉的東西一件件修好。
「修理東西不能光靠蠻力,」阿公總是一邊轉動收音機的旋鈕一邊說,「要聽懂它想告訴你什麼。」那天收音機雜音很大,阿公沒有急著拆開,而是先輕輕拍打外殼。當拍到右下角時,雜音突然變小了。「你看,是裡面的電線接觸不良。」他笑著遞給我一顆水果糖,糖紙窸窣的聲音和收音機裡突然清晰的歌聲混在一起,成了我最難忘的記憶。

阿公修東西有自己的規矩。補腳踏車內胎時,他一定要先盛盆肥皂水,把漏氣的地方找得明明白白;修理木椅前,總會用手摸遍每個榫頭,說這樣才知道哪裡「生病」了。有次我的機器人玩具不會走路了,阿公花整個下午拆開又裝上,最後在齒輪間找到我掉進去的橡皮擦。「修理就像看病,」他用棉籤蘸機油擦著齒輪,「要對癥下藥。」
街坊鄰居都愛找阿公幫忙。三樓阿婆的電鍋不會跳保溫,阿公換了片磁鐵就搞定;對面早餐店的收銀機常卡紙,阿公教老闆用爽身粉潤滑齒輪。最神奇的是有年颱風天,整條巷子停電,阿公竟用摩托車電瓶接上檯燈,讓巷口雜貨店能繼續營業。
上個月回家,發現阿公的工具箱蒙了層灰。
原來社區來了位年輕水電工,騎著印滿廣告的機車,帶著閃亮的新工具。「現在人都喜歡換新的,」阿公摸著陪伴他三十年的水平儀,「說修理太麻煩。」但那天晚上,他還是偷偷修好了我掉進馬桶的手機——用牙刷沾酒精清潔電路板,再用吹風機低溫烘乾。
昨天經過巷口,看見那個年輕水電工蹲在阿公旁邊,兩人正在研究一台老電扇。「前輩,」年輕人指著鏽住的軸承,「這個是不是該噴潤滑劑?」阿公搖搖頭,從口袋掏出半截蠟燭,在軸承上來回摩擦:「蠟油更持久,而且不會沾灰塵。」
我突然明白,阿公的修理哲學從來不只是修東西。就像他常說的:「物件跟人一樣,用真心對待,它就會用壽命回報你。」現在我的包包裡總放著阿公送的小螺絲起子,每當同事的手機殼鬆了或眼鏡螺絲掉了,這把起子就會派上用場。而每次轉動它時,我彷彿又聽見阿公工具箱裡,那些老工具互相碰撞的叮噹聲。
文章未完,點擊下一頁繼續